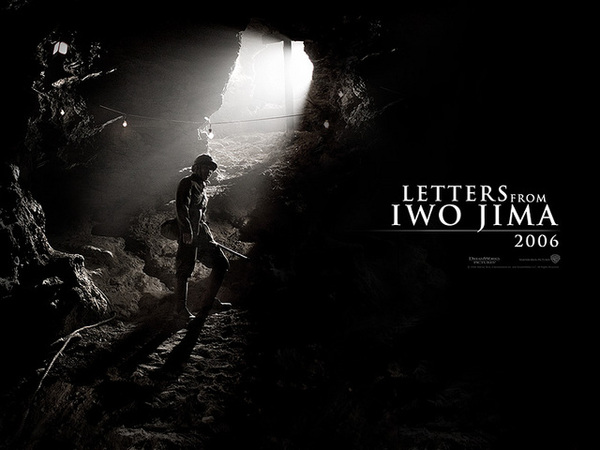世界餐桌----食物旅行家
當《享受吧 一個人的旅行》遇到了《深夜食堂》,最後總會發現,食物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like
2018年6月6日 星期三
2017年8月15日 星期二
土耳其餐桌--愛貓之城
*愛貓之城*
看了土耳其紀錄片「愛貓之城」,在伊斯坦堡玩貓的記憶全回來啦。
那些釣魚的中年虯髯漢子,看似Man的不得了,但一遇到腳邊的貓,幾乎化成一灘水,不管有沒有魚兒上鉤,每個釣魚人都愛蹲下身來愛撫貓咪,泛著青筋的粗糙大手摸著貓咪柔軟的毛皮,嘴中喃喃細語,神色溫柔。
貓是一種認為自己是神的動物,淡淡忍受中年大叔的反差萌,慢條斯理等著吃魚。
全文請看
2017年8月6日 星期日
2017年2月19日 星期日
2016年8月29日 星期一
請大家來點光明燈喔
SOS是一個新創網路內容平台,讓讀者可以定期小額資助喜歡的創作者,員工平均年齡才二十多歲。
辦公室位在松煙的閱樂書店後方一個走廊般的空間,幾個年輕人排排坐,對著電腦工作,外頭的行人由窗子望進去,還以為是個網咖。
他們不需要多大的空間,不需店面、倉儲、廠房,因為他們的商品就是人類腦中的結晶。
我覺得,SOS這一小方天地,或許是整個松山文創園區最有活力的地方,比松煙誠品裡閃閃發亮的店面「文創」多了。
台灣人尋租成癖,對文創產業的想像貧乏,還停留在弄個園區、店面就搞定了的石器時代,乾脆設廠辦買機器算了。創作者最需要的不是物理空間,給創作者一個園區何用?商人才付得起房租啦。
台灣從來不缺優秀的創作者,我們缺的是能讓作品變現的商業機制。再好的創作,無法變現,就沒有商業價值可言,沒有糧草繼續走下去。
出版崩壞已經是事實,紙本書彷彿二十世紀初期的馬車一樣。原本的消費者去哪啦?去打怪、上網、抓夢可寶,文靜的書頁要面對五光十色的競爭。
但這不是世界末日,書寫的介面曾經是石頭、粘土版、竹簡、絹布,故事仍然存在,只不過是從紙本書換成0與1罷了。
而透過網路直接讓第一線的創作者和受眾互動,也只有像SOS這樣的數位原住民有本事。
我大學念的是政大新聞,很多同學至今在傳播業搖筆桿,但其實我一開始對寫作沒有什麼綺麗的想像。
因緣際會,我不過是在上下游網站寫點關於食物和旅行的故事,可能編輯們本來就比較屬於友善農產品的客群,會在上下游出沒,我還寫不到兩篇,好幾家出版社陸續找上門。
承蒙不棄,和我合作的出版社都很有規模。第一本書被選為誠品選書,第二本書很快賣出外文版權。這條路上,我沒什麼懷才不遇、煮字療飢的遭遇可說嘴。
說白一點,就是超級幸運。我知道自己特別幸運,所以更要將幸運分享給其他人,尤其分給更年輕的作者。
小額資助聽起來點像去廟裡點光明燈。創作的實質報酬不高,貴在精神上的滿足。但如果我的參與能讓平台賺錢,順利營運下去,那將有更多作者有機會被看見。
動人的文字本來就是一種心靈撫慰,就像去廟裡拜拜一樣。
所以,就算是光明燈也好,請大家來點一盞吧。
我一直對飲食和旅行懷有熱情,並有個歐巴桑般的嗜好---不愛逛百貨公司,反而喜歡去當地菜市場繞繞。
俗話說「歪嘴雞,吃好米」,但我這隻雞不管什麼米,都懷著好奇心吃下肚,興致滿滿,因為吸引我的是食物背後的故事。食材在哪裡生產,怎樣的風土人情才孕育出這道菜,怎麼煮,如何吃,什麼時候吃,和誰一起吃.........。
食物連結天地自然,承載情感和回憶,酸甜苦辣熬煮成一鍋,我們稱之為「生命」。食物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我即將在SOS展開新的寫作計畫,深入探索更多異國的餐桌,望你能給我更多意見:http://pics.ee/LQI
食物連結天地自然,承載情感和回憶,酸甜苦辣熬煮成一鍋,我們稱之為「生命」。食物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我即將在SOS展開新的寫作計畫,深入探索更多異國的餐桌,望你能給我更多意見:http://pics.ee/LQI
請幫我分享,謝謝^^
2016年1月19日 星期二
台灣餐桌---移工的虛擬故鄉
「第一廣場小書攤」的志工除了每週日擺攤借書給移工朋友之外,還舉辦導覽活動,帶領臺灣人用新的眼光探索第一廣場。多年沒來,我發現移工和新住民在這打造了一個虛擬故鄉。
盼了又盼,發薪日後的第一個週末,他們興沖沖出門,換髮型、選手機,採買衣鞋、菜蔬醬料、老家的泡麵。許多移工搭火車、巴士前來,坐在懸掛自家國旗的小吃攤,用熟悉的飲食味覺劃出國界,進行一趟返鄉小旅行。
這裡有印尼炸物和沙嗲、越南河粉和三明治、菲律賓燉豬肉和哈囉哈囉冰、泰國冬蔭湯和木瓜沙拉,還有南薑、檸檬葉、椰奶、咖哩、香料、 香草、魚露、香茅、辣椒、羅望子。他們是否還有點想念臭魚、蝦醬和 鴨崽蛋呢?聽他們開懷高歌卡啦OK,咀嚼的是歸屬感,吞下的是思念,食物是一盤盤破碎的鄉愁,暫時把他們帶回湄公河或蘇門達臘、紅河平原或呂宋島。
臺灣人的世界只有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反而不認識這些近在咫尺的鄰居。唱歌、吃飯、聊天,說母語時才不用屏氣凝神,他們來這裡深呼吸,放聲大笑,吃好料打牙祭。
很累呀,真的。他們彎腰擦地、洗碗,哄小孩乖乖吃飯,幫老人換尿布。他們進工廠、入工地,上船捕獲臺灣人冰箱中的海魚。手機用久了都要充電,移工當然也需要休息。
不管他們家鄉在哪,全被叫外勞。在臺灣人眼裡,外勞全差不多,其實他們差超多的。不,沒有人的名字叫外勞。 他們可能叫瑪利亞,來自菲律賓,目標是蓋房子,好讓成群兒女不用再拿碗公接雨水;可能叫阮國安,來自越南的離島,在漁船上如履平地;可能叫媧洋,來自印尼,排行老大,希望供弟妹上學;可能叫通,泰國農村的綠手指,擠在工廠宿舍,仍種了兩盆蘭花,偷偷崇拜美麗。
他們有20多歲的強健體魄,30多歲的耳聰目明,從破敗凋零的鄉下村子出走,第一次坐飛機就飛到這個島嶼,第一次出國就久得讓人嘆氣。女人把滿腔溫柔留給別人家的寶貝,忙著推別人爸媽的輪椅,男人填補了工廠、農田、工地、漁船上空蕩蕩的位置。
故鄉雖然永遠可以回去,但回不去那段缺席的時光。他們用生命換取金錢,金錢卻買不回生命,小孩被時間偷走,換來陌生的青少年,回鄉時相顧無言,誰也不認識誰。他們賺來的血汗錢用來付學費、養生送死、治病療傷,盤算多時,買這買那,剩下的錢,偶而來第一廣場吃一碗牛肉丸或河粉湯。
雇主的一念,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獄。 媧洋照顧的老阿嬤可能不認得兒女的臉,但仍一心掛念媧洋不吃豬肉。國安的船東或許對他的創傷不聞不問,任他感染發炎,痛苦哀號。臺灣人似乎刻意跟他們隔著一段距離以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免於什麼呢?
我想,或許是貧窮吧。不好意思,他們既然身在這裡,就無法隱形。總不能只要勞動力,卻不要勞工吧?他們默默無聲,嘴裡吐不出幾句話,但心中歡聲盼望過開齋節、聖 誕節、潑水節、農曆春節。他們的行李很 輕,裡面只裝著夢想而已。沒有人想離鄉背井,除非遠方充滿希望。
臨行前,他們向觀音菩薩點香,向四面佛頌念,向阿拉真主叩首,輕聲細語,要求從來不會很多。說到底,他們和你我一樣,為了家人,為了一口飯,終日奔忙。唯一不同,就是他們來自異國他鄉。
2015年12月21日 星期一
西班牙餐桌----跳佛朗明哥的補鍋匠
在西班牙南部的格拉那達時,被友人荷西帶去一個小小的佛朗明哥party,來的只有餐廳的老主顧,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
這場子不是給觀光客的娛樂,而是當地人的同樂會,耳朵一聽到熟悉的曲調是會起共鳴的。
西班牙人天生有享樂的本事,歌舞到酣處,觀眾和表演者的距離都消失了,台上台下一陣搖頭晃腦,啞著喉嚨低聲吟唱,白髮蒼蒼,腳踏掌擊,節拍仍抓得準準準。
我說:「聽他們的歌聲,好像在承受人生巨大的悲哀似的。」
「當然,」荷西說:「這幾個表演者都是吉普賽人。那種腔調和情緒是血裡帶來的。」
佛朗明哥誕生於吉普賽人長年的顛沛流離之中,他們四處流浪,以馬車為家,晚上圍在營火旁吃大鍋菜、說故事,興之所至,就來段即興歌舞,身影就著火光,映在岩壁或馬車篷上。
他們耳濡目染,打從邁出第一步,就會跳舞,一學會說話,就會唱歌。吉普賽人的歌舞不為賦新辭強說愁,不精緻華美,也不典雅蘊藉,只有歷經困頓磨難而不屈的生命力傾洩而出,酣暢淋漓。
對我來說,吉普賽人好像不該在現實生活中露面,只應帶著水晶球和塔羅牌出現在電影小說裡。
看我骨碌著兩隻眼睛,好奇不已,他們說:「吉普賽人對現代社會的適應程度不一,有的人只把馬車改成露營車,走的還是漂泊的老路子。有的人改行,有的人更慘。」
「多慘?」
「定居就學,畢業後去上班領薪水,乖乖繳房貸、車貸。」
「Oops……..真的很慘。」我口中喃喃附和,在台灣再自然不過的生活常軌,在他們眼裡卻是悲劇。
畢竟是追求心靈自由的藝術家,佛朗明哥是他們的翅膀,吉他聲、舞踏聲、嗓音,其實是舞動翅膀的聲音。
我說:「你們就像鳥兒在飛翔。」引來他們大笑。
「那你們的先人飛累了,通常吃什麼?」
「這個嘛…….很值得一提的倒是沒有.....因為吉普賽人通常很窮,有什麼吃什麼,飲食沒什麼講究。」
我問:「你們過年過節吃什麼特別的食物呢?有食譜嗎?」
看我聽得一愣一愣的,笑道:「哈哈,其實還不是因為窮?窮人有什麼吃什麼,全加到大鍋裡煮。哪需要食譜?」
「我祖母老家就鑿在亞爾漢布拉宮後頭的山壁裡,我小時候去,都吃大鍋菜,不管什麼食材,馬鈴薯、蕪菁、洋蔥,偷獵的兔子雉雞,林子裡採的野菇,洗洗切切丟進一個古老的大鐵鍋就是了,一鍋煮到底,不用其他烹飪道具,是最簡單豪邁的烹調方式。印象中鍋子從來不洗,也不曾見底。」
「那這樣夏天不會壞掉嗎?」
「鑿在山壁裡的石洞,冬暖夏涼,炎夏一踏進去,溫度驟降。而且窮人哪有挑挑撿撿的餘地。」
「不過,我們的先人雖然對鍋子裡的食物不講究,卻是走遍千門萬戶的補鍋匠。」
他們指著餐廳牆角淪為擺飾的鐵鑄大黑鍋說:「在不鏽鋼的鍋具大量生產前,家家戶戶的鍋子破了壞了,都委託我們帶著活動的風箱和冶煉工具,幫忙修補焊接的。」
「以前的平民再怎麼家徒四壁,屋裡還是有一口鐵鑄鍋子,畢竟是吃飯的傢伙。而這唯一的鍋子可能是這戶人家最有價值的物品,一旦壞了,一定要補。」
吉普賽女人精通草藥,男人擅長冶鐵,要行遍天下,必須身懷實用的技能,不只是風花雪月而已。
我邊看著近在咫尺的歌舞,邊低聲和荷西咬耳朵:「他們哪是在唱歌跳舞?這是在燃燒。燃燒到極致,昇華為一場奇妙的宗教體驗。」
荷西聽了我的心得,笑說:「這也不奇怪,你聽佛朗明哥時,會忘我的大喊OLE(歐類),OLE其實來自ALLAH(阿拉)的轉音,十五世紀以前格拉那達由伊斯蘭文化主宰,藝術家出神入化時,是蒙神庇佑,與阿拉真主同在呀。」
2015年10月29日 星期四
在異國餐桌上旅行 新書分享會 來吃鹹派吧
* 在異國餐桌上旅行 新書分享會*
日期:11/1 (日) 14:30~16:30
地點:台中市 青木和洋食彩
地點:台中市 青木和洋食彩
佛心來著的朋友怕我真的去賣大腸麵線,幫我辦另一場新書分享會。
青木餐廳會準備書中出現的食物喔,讓來賓一邊吃一邊聽,一邊聽一邊吃。
想吃吃看書中出現的庫德紅茶,法國鹹派,印度牛奶糖嗎?
什麼?聽演講時沒吃過東西?
2015年10月21日 星期三
讀書心得報告---- 耶路撒冷的移住者
2015年五月 商周出版
by立皮卡佩拉漢
以色列於1967年的六日戰爭攻下耶路撒冷以前,「明年耶路撒冷見」曾是漂泊無根的猶太人彼此安慰問候的傳統用語。
耶路撒冷,讓風中浮萍般的猶太人懷念了兩千多年的心靈故鄉。
都說相見不如懷念,那終於在耶路撒冷見了以後呢?
《耶路撒冷的移住者》說的正是BBC女記者跟著猶太夫婿搬到耶路撒冷的生活點滴。
以色列建立在數千年的信仰上,復國歷史卻比很多賣炸魚薯條的倫敦小吃店還短。
當地的飲食特色就是沒有特色,端看你的祖父母當年從世界的哪個角落搬回來。除了「奶肉不混吃」、「不吃豬肉」、「鮮肉要沖水抹鹽去除血水」之類的飲食禁忌,沒有共同脈絡,不遵循風土節氣,情感尚待累積,喜好仍需沈澱,以色列餐桌是個生硬的大拼盤,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
以色列人說的希伯來文,曾經只有猶太拉比(祭司)在禮拜祈禱時才頌念。神聖歸神聖,但如同拉丁文或梵文,已是死語。
為了避免以色列分裂成不同語區,復興希伯來文成為首要國策。畢竟猶太人的唯一共同點就是根植於經文中的信仰。
於是希伯來文從創世紀一開頭「這裡要有光!」的天啟神諭,透過語言學家和教師的努力,變成普羅大眾口中「媽,廁所有衛生紙嗎?」這種日常對話。
受苦流浪了兩千年多的猶太人,手握權力後,讓另一群人開始受苦流浪。受害者因為心理補償,往往是最殘酷的加害者。
以色列孤傲地與伊斯蘭鄰居為敵,在中東地區「流著美國血液,跳動著一顆歐洲心臟」,樹立敵人的速度比消滅敵人的速度還快。
出入國境的安檢盤問不休,唯恐每個阿拉伯青年的生平愛好就是挾持飛機去撞大樓,或是去購物中心放自殺炸彈。
曾有剛退伍的以色列女生對我說:「這不是正常的生活。當我們受夠時,會彼此揶揄,如果當初選了烏干達呢?非洲東部的烏干達曾被列為猶太復國的選項之一。」
「對耶,如果當初選了烏干達呢?(What if Uganda?)」
「親愛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烏干達不是應許之地,沒有耶路撒冷。」
本文收錄於小日子雜誌。
PS結果藉由閱讀這本書,回想起和以色列旅伴的對話,寫了
以色列餐桌---流浪的味道,收錄在新書在異國餐桌上旅行裡。
2015年10月20日 星期二
德國餐桌---黑麵包童話

在德瑞邊境的農場小住時,我常被派去村裡的麵包店要滯銷的老麵包,磨碎當動物飼料。
客人上門只買剛出爐的新鮮麵包,隔夜麵包像機票,過了起飛時間就不能賣。富含精糖、奶油、牛奶、雞蛋的白麵包不適合動物吃,因此我來回用三輪推車搬運了這輩子從來沒看過的各式黑麵包。
我發現做麵包一定要照本宣科,按部就班,不然就不能冠上這款麵包之名。即使外觀神似,只要比例、食譜不一樣,按照法規就不能亂叫,據說登記在案的起碼有幾千種,極具特色。
德國地處小麥和雜糧的交界,麵粉加入黑麥、大麥、燕麥等等雜糧,無數種排列組合,造就出自豪的黑麵包文化,一板一眼的德國人做起麵包,自然有板有眼,2014年起已名列世界遺產。
老師傅做出來的黑麵包,是一塊可以啃咬的傳統。
麵包執照和糕點執照不同,糕點常有女人染指,而麵包烘培多半仍是男子漢的神聖領域,當別人好夢正酣,虎背熊腰的師傅們就開始漏夜揉麵,費時費力,遠從中古世紀就有職業公會。
麵包店的孫女安娜說:「揉麵需要腰力和臂力,在機器發明前,父傳子、子傳孫。」
安娜剛從巴黎學完甜點回來,夢想存錢開一家甜點咖啡廳。她在父親、祖父補眠時,邊顧店邊和我閒嗑牙。
安娜倒出一堆大大小小的黑麵包,我嘆道:「這麼多種類。真了不起。」
「對呀,只用雜糧粉、麵粉、水、酵母、鹽巴。」
「就這些?」
「沒別的。」
「真的?」
「時間,還有時間。沒耐心就沒好麵包。」
安娜常把試做的甜點帶到農場來,看我在穀倉前把麵包切成小塊,麵包屑散了一地,成群的雞鴨鵝蜂擁而上。
黑麵包像沉甸甸的磚塊,幾乎能砸死人,切起來很費勁。
安娜打趣:「小心呀!麵包屑被鳥兒吃完,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糖果屋是嗎?」我回嘴:「我不信漢斯和葛蕾特丟麵包屑沿路作記號,爸媽窮到連小孩都養不起了,吃的一定是硬梆梆的隔夜黑麵包,不是白麵包,小孩的手怎麼剝得動?」

「再說,要認回家的路,沿路攀折花草、甚至在樹幹上作記號,不是更好的選擇嗎?怎麼會笨到把僅有的麵包丟在路上呢?」我問。
安娜說:「童話不是給小孩子看的,那是反應了集體潛意識的民間故事。」
德國人注重腦袋、不注重胃口是出了名的。童話快樂結局裡的盛宴頂多幾句「從沒見過的山珍海味」草草帶過,唯獨糖果屋這個故事,從頭到尾都在講口腹之慾。
出於飢餓,繼母慫恿父親把小孩丟棄,出於飢餓,小孩拆下巫婆的糖果屋大嚼,而巫婆抓小孩不為別的,就是要養胖打牙祭。
所有的角色都像動物一般,被最原始的飲食本能驅動,而不是抽象的虛榮、志向、愛情、好奇、野心。
安娜說:「糖在古代是昂貴的舶來品,甜點代表奢侈的耽溺和危險的誘惑,試探人性的弱點,誘人犯罪,陷於兇惡。而麵包,在宗教上代表耶穌聖體,對我們德國人來說,麵包是每天日用的食糧,神賜的生命,代表道德,代表父神的權威,父土的國魂。」
丟麵包屑為糖果屋埋下了伏筆,一旦麵包屑被野鳥啄食殆盡,偏離日常的軌跡,魑魅魍魎現形,群魔亂舞,一棟糖果屋赫然聳立在黑暗森林裡,妖氣衝天。
我說:「黑麵包太酸太硬了。我吃慣Q軟的米飯,還是喜歡白麵包的口感。」
「就像點心零食。」安娜說。
我說:「沒錯。麵包對我來說不是正餐。麵包剛傳到亞洲時,只賣給有錢人,用得起牛油和細麵,歐洲庶民賴以維生的黑麵包反而少見。小麥隨著二戰後源源不絕的美援進入台灣飲食,用不著混入五穀雜糧。標榜健康自然的歐式手工黑麵包出現在貨架上,也不過近十年而已。」
安娜說:「老德國人出遠門都要帶幾塊家鄉的麵包,就怕吃不慣。但是,唉,你最清楚我們店每天滯銷多少麵包,年輕人不那麼講究風味口感,機器製造的又便宜。做傳統麵包,吃力不討好。」
「我只想開法式甜點咖啡廳,更讓我爺爺痛心疾首。」
我說:「彷彿大家都被糖果屋迷惑了………對吧?」
「也有人說這個故事,反應了女性陰暗面。」安娜說。
「哪有?這故事唯一的英雄就是葛蕾特,敢和女巫單挑呀。」

* 在異國餐桌上旅行 新書分享會*
日期:11/1
地點:台中市 青木和洋食彩
地點:台中市 青木和洋食彩
本文刊登於本期好吃雜誌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89337
2015年9月29日 星期二
台灣餐桌---生還的咖啡香
當一個小伙子漸漸白了頭髮,他就失去了名字。
全世界都叫他阿公。
全世界只叫他阿公。
年輕一輩總有個錯覺,彷彿老人一直以來都那麼老,安詳縮在一角靜靜喝茶,不曾驚恐、不曾徬徨、不曾痛哭、不曾情話綿綿。
好似對人生已經了然於胸,波瀾不驚。
阿公說他喜歡茶,但更喜歡咖啡。
對他而言,咖啡是生命的味道。
(photo by青木)
因為他曾在美軍管轄的日本戰俘營的咖啡香中,一次又一次確認自己不會在天搖地動中被炸成一團模糊的血肉。深深感謝老天爺保佑,讓他能從這一場惡夢中甦醒,咖啡打開他的雙眼,恢復神智,不再繼續夢遊下去。
他知道終於安全了,他等著回家,回到父母妻子的身邊,把沒見過面的兒子抱在懷裡。
當他入伍時,兒子還沒出生呢。
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軍節節敗退,兵源短缺,殖民地台灣的成年男子終於有了成為日本皇軍的天大殊榮。
有人怕戰爭太快結束,唯恐榮耀沒自己的份,一頭熱的在入伍志願書上蓋了血手印,甚至用毛筆沾了自己的鮮血,整篇忠君愛國、武運昌隆,只求穿上英挺的軍裝。
他們最終如願地在萎靡破敗的太陽旗下,用鮮血來償還這股莽撞的傲慢。
相反的,在昂揚軍歌也悄聲的半夜三更,有人咬牙自殘,有人拋妻棄子遠走海外當逃兵,有人改行投入林業礦業,想方設法避免被征招。
他盤算再盤算,農人被土地綁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恭喜恭喜。是堂堂的軍人,不是軍伕。多麼光榮的事。」兵單送到門口,妻子面無表情接下,手撐著腰,轉身抹下眼淚,胎兒在她腹中拳打腳踢。
他好不容易說服妻子:「這場戰爭,我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與其最後被征招上前線當砲灰,白白送死,不如趁早自願入伍,搶個安全的文職好缺,還有一份軍餉,你做為軍眷也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糧食配給。」
不管對戰爭熱情澎湃或是冷眼旁觀,沒人敢說戰爭的壞話。戰爭變成了神明一樣,不,像天皇一樣。
渴望和平這種話萬萬不可說出口。甚至連抱怨戰爭帶來的種種不便,也會被特高(祕密警察)當成「非國民」盤查肅整。
男子漢的最大罩門與其說是不愛國,倒不如說是怕被人譏笑膽小怯懦。
愛國婦人會的婆婆媽媽們低頭縫紉,趕繡歡送出征的布條。他高高騎在馬背上,整個村子的老小都沿街歡呼送行,高舉雙手呼喊萬歲。
他飲下餞行的清酒。
他會回來。
他一定會回來。
故鄉有人在等他。
遠在東京的軍部武人獨斷獨行,暗殺數任總理大臣,掌控內閣,綁架國會,和大財閥勾結,完全不受制衡,像玩大富翁似的紙上談兵,自己從沒上戰場流過一滴血,倒是慷慨激昂地動員無辜青年去白白送死,打算靠白日夢打贏這場必輸的戰爭。
於是,毫無選擇的,他的血肉靈魂成了讓這台瘋狂的軍國機器繼續運作下去的廉價燃料,甚至連最卑微的零件都算不上。
(電影 來自硫磺島的信 劇照)
他被派到菲律賓的小島,他知道他翻譯傳遞的軍令一半是謊言,他試著從另一半拼湊出現況。
所謂的軍事通訊就是互寄謊言,作戰大本部的報告全在胡扯亂吹,先把夢話說到連自己也信以為真,再把全體國民蒙在鼓裡。
他對戰爭不抱夢想,所以沒有幻滅,他只默默可憐那些被熱血燒壞頭殼的傻子,不惜缺手斷腳只為爭取泡沫一般的戰功——「只有受傷第一個月你是英雄,接下來你永遠就是個普通殘廢。」
現實比謊言更不堪,制空權早已失去,他每天抬頭絕望地望著無數美國軍機往北飛去,噪音幾乎劃破耳膜,是去轟炸台北高雄嗎?還是東京大阪?
海軍艦隊全數被擊沈,美軍封鎖了後勤補給線。桌上伙食是末日戰局的縮影,缺米缺糧,連高級軍官都只有蕃薯藤吃,為了合乎規定,還多擺上幾個空盤子充數。
什麼都沒了,用來洗腦的謊言倒是十分充裕。
「明明那麼多明眼人,都在作夢嗎?竟然從沒想過日本會輸嗎?」當然他無法說出口。
最後連鹽巴都沒有了。
除了麻木,就是飢餓,每個人雙腿發軟,空著肚子被海風吹得腳步不穩。挖墓是例行公事,閒來無事就是寫家書,家書常常就是遺書,還得寫得言不由衷,多麼樂意為天皇去死,唯恐被挑出什麼毛病,戰死了還給家人添麻煩。
指揮官吐著唾沫星子,發誓要戰到最後一刻,把生命獻給天皇陛下。「反正被美國人俘虜,也左右是死。時候到了,就自殺吧。是男人就別不知羞恥苟活於世。」
他心中默默頂撞:「我不會死在這裡。我不要死在這裡。」
不管是小林、田中、高橋、井上還是松下,他們死前喊的才不是「天皇陛下萬歲」,而是「媽,我想回家。」
他發誓他將安享天年。在很老很老的時候,還在祖先開闢的土地上耕種,忙著除草澆水—–「我會回去看我第一個孩子,我還會有其他孩子,兒女成群,孫輩曾孫輩共有幾個,記都記不清。」
他會死。
但不是現在。
不是這裡。
他來自溪水潺潺的蓊鬱山林,他的墓不會在這個鳥不生蛋的孤島上。
(電影 來自硫磺島的信 劇照)
大海茫茫,瀲灩著波光,豔陽灼人。這場戰爭是一顆將他拖入深海的鉛球,他口吐氣泡,舉目仰望頭頂上的光,沉,沉,沉,深不見底。
日本挨了兩個原子彈後,無線電傳來天皇宣佈戰敗的玉音,像把斧頭應聲砍斷鐵鍊,他搶在斷氣之前,踢腿浮上海面,深深吸了一口氣。
日本無條件投降,一切都結束了。玉碎、切腹、犧牲、大義、為國捐軀,什麼去你媽的鬼話都不用再聽了。
少數對戰敗感到絕望的人,面向天皇所在的北邊,雙膝下跪,謝罪自殺了。
他們流下悲憤的淚,永遠閉上雙眼,看不到日本在短短二三十年後做為經濟大國的再起,也來不及理解,戰敗對小老百姓來說或許是種解放,從戰爭販子手中解放。
大多數人被送到戰俘營裡等待遣返。戰俘營裡的伙食好得驚人,奶油、麵包、牛肉罐頭,每個人都像吹氣似的胖了起來。
他每次吃飽飽的,總不免想到:「早知道就早點投降,英美鬼畜根本沒有宣傳中的可怕。」
每天還有一大桶像青草茶的藥湯,黑黑的,苦苦的。
要加奶精,要加糖。
大匙的白糖。
白糖?投降前日軍連鹽巴都沒有,他奉命挑海水來煮鹽,鐵鏽染黃了鹽結晶,黃黃髒髒的。他暗地裡用鹽和島民換了私房菜吃。
聽說美軍還在歐洲戰場空投糖果包裹,瓦解納粹德軍的抵抗。
他終於收到故鄉南投的家書,第一個孩子早已出生,是兒子。
「我還活著。感謝老天,他不是我的遺腹子。」他們高舉裝滿咖啡的行軍鋼杯來乾杯慶祝。
「在日本內地有很多咖啡廳呀。台灣沒有嗎?」一名同袍問。
他自然曾聽說戰前在台中州廳火車站前,開了幾家時髦的咖啡店,爵士樂聲中,女服務生頭髮捲得翹翹的,蕾絲圍裙下一雙雙筆直圓潤的小腿,蹬著高跟鞋。
黑狗兄黑貓姊久久坐火車去啜飲一杯咖啡,裝模作樣,模仿漂亮的東京口音,炫耀自己摩登又風神。
只不過,他不知道美國人天天喝咖啡。好像不喝咖啡就不會飽。
他慢慢學會喝咖啡。就像茶一樣,咖啡不是用來配飯,是用來閒嗑牙的。
(photo by青木)
美國大兵給家中太太寫信,總是說前線一切順利,除了暴雨、烈陽、泥濘、地雷、砲彈、刺槍、空襲、鐵刺網、豬頭長官、新傷加舊傷、截肢、感染、尖叫、惡夢以外,戰爭真的沒什麼,只是輕而易舉的一塊小蛋糕(a piece of cake)而已。
而蛋糕配咖啡,再適合也不過了。
美軍弟兄日日都為發明即溶咖啡的那位天才禱告。只有上帝才知道一杯熱咖啡在戰壕中能帶給人巨大的鼓舞和片刻的安寧。
軍用即溶咖啡只能解癮,聽說真正的好咖啡講究現磨現煮,烘培咖啡豆就像製茶一樣講究,於是他開始對咖啡有了興趣。家鄉的田可以種茶、種稻米、種香蕉,那有天能不能種出咖啡來呢?
他從菲律賓回到家鄉的那一天,兒子邁著小胖腿向他跑來,這個陌生人身上有一股特別的味道。
幸運的小伙子沒缺胳臂沒斷腳,鼻腔吸入了足夠回味一輩子的咖啡香,註定將老死在家中的床上。
更奇怪的是,他竟然成了戰勝國的國民,他去打的那場戰爭不是明明輸了嗎?他迷失在這個矛盾的謎團裡,失去了聲音,從此很少對外提起被派去南洋當兵的陳年往事。
他對咖啡朝思暮想,是一輩子的愛戀,從惠蓀林場要來幾株咖啡樹,自己慢慢摸索,就算轉作歷經重重困難,水土不服,從種子開始培育的幾千株咖啡幼苗全死光光,什麼豆子都長不出來,也不改變心意。
(photo by青木)
阿公已高齡九十多,他攝取了足夠的咖啡因才去午睡。
孫兒、曾孫在咖啡樹下奔跑玩耍。兒子照料咖啡園,紅豔豔的咖啡豆引來許多好奇的野鳥,採摘、剝皮、發酵、日曬、去殼、烘烤、研磨、沖泡。
種咖啡的好處是永遠有人上門來聊天,阿公一邊啜飲著自己土地種出來的咖啡,一邊訴說當初怎樣在戰俘營中迷戀上咖啡的味道。
一股好感全湧上心頭。
那不是大正時期文明開化的異國洋味,而是慶祝生命的味道。
(二戰結束70年,感謝 國姓梅林咖啡 分享家族口述歷史)
新書熱買中 在異國餐桌上旅行(商周出版)
訂閱:
意見 (Atom)